殖民者離開後,就能獲得完全的自由了嗎?
2018 Apr 26 認識非洲
作者:中東研究通訊

20世紀中期,許多亞非國家終於掙脫了殖民者的統治,而熱情高漲的人們在度過最初那段相信自己終於擺脫了外來者的壓迫、獲得了自由的時間之後,漸漸意識到自己其實與殖民遺產不可分割。
長期以来,領土、空間和土地等概念都被賦予了特殊意義,那是某種帶著濾鏡色彩的、關於家鄉的、擁有共同歷史和未來的象徵性記憶。早期的民族主義者們通過對自己土地上文化的闡述,以此與他者區分開來,體現我們與他們(殖民者)的差異。而差異的建構首先需要建立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身份認同和主體性,很多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在國家建構中便面臨這樣的挑戰,即無法將領土内不同文化、語言和種族的人凝聚在一個安德森式的想像的共同體内。
不僅如此,還發現自己與想要區分開的殖民遺產緊密相連。這既否定了空間創造記憶、記憶或延續的歷史構建身份認同這被認為是自然存在的關係;還提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當我们試圖理解人類體驗時,我們與他者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到底該如何被理解?

(蘇丹鄰近紅海,近非洲之角。/ 圖片來源:wikimedia)
蘇丹(Sudan)為我們提供了一條思考路徑。在歷史上,「蘇丹」一詞並不具有民族主義者賦予它的現代意義,也就是說,它並不指代某一片邊境明確的領土或是某一個具體的政治和文化的共同體。
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學家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區稱為黑人的土地(Bilad al-Sudan),阿拉伯語中 Sudani 一詞意為「黑色的」。在英埃統治下的蘇丹,幾個世紀長的奴隸貿易使得「蘇丹」一詞有了其他社會意義。對於北部說阿拉伯語、自我認同為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們來說,作為蘇丹人意味著是黑人、奴隸或著說來自奴隸家庭,有更低的社會地位。
1928年,Khidir Hamad 賦予了「蘇丹人」新的意義。受埃及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畢業於戈登學院 Gordon College(這是英國人為培養政府官員而創半的學校,大部分學生來自於北方政商界有聲望的家庭)的他在申請政府工作被問及其所屬部落,答道「蘇丹」時,對方堅持詢問部落名字,他說:「那是你的事,我們不知道什麼部落,我们只知道自己是蘇丹的兒子」。此舉在當時備受爭議,來自於同一圈子的人也猛烈地攻擊他。
蘇丹民族主義自此埋下伏筆。早期的民族主義者們,多家境優渥。從戈登學院畢業後進入殖民政府工作,成為帝國政策正常運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作為本土精英,他們在殖民政府中的晉升困難和受到的排擠,以及20世纪初那股刮得強烈的民族主義的風潮,使得他們越來越相信蘇丹應該獨立,這個國家的命運應該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一批民族主義者站在抵抗英國殖民统治的最前線。
然而,他們的成長背景和個人身份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其眼中國家或民族含義的一部分,提倡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教,將其作為政策制定和構建民族集體認同的基礎;不僅如此,英國曾經建立的執政模式和行政機構也遺留了下來,這些都成為了這個種族、文化、宗教和語言都十分多樣的國家獨立後國家構建過程中的主要障礙。
在這個背景下,蘇丹作家塔依卜·薩利赫(Tayeb Salih)的小說《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中文譯名:《風流賽義德》/《移居北方的時期》),講述了在後殖民時代的蘇丹,個人與時代的不可分割性,或者說,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互相定義、互相依存的關係;講述了後殖民時代中歷史的矛盾心理和個人身份的複雜性。
(蘇丹作家塔依卜·薩利赫的小說《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 圖片來源:NYR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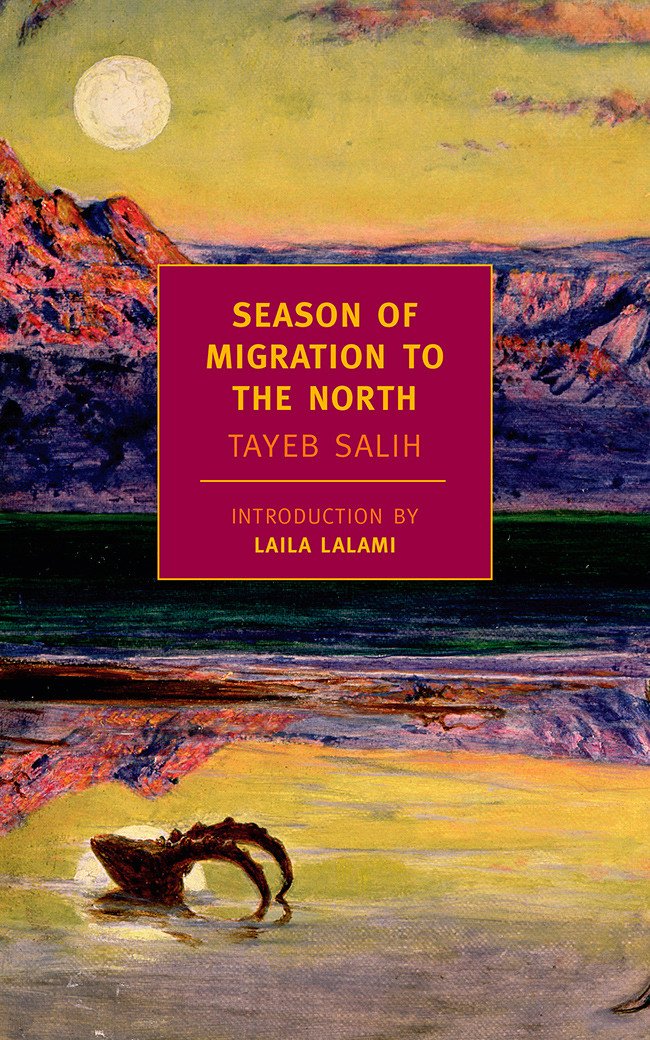
「我」到底是誰?家鄉還是那個家鄉嗎?
故事中的「我」從倫敦結束學業後回到自己的村莊,認識了賽義德。由這兩人展開交叉敘述,蘇丹和倫敦的景象交替出現在讀者眼前。「我」得知賽義德早年拿到殖民政府的獎學金先後於開羅和倫敦學習,後回到村莊娶妻生子,慢慢也了解了他的秘密。
賽義德難以安頓、融入於此。在倫敦時,他玩弄女人,操弄著英國女人那東方主義的對於異國情調的幻想和渴望。他將自己展現為來自非洲的狂怒之人,向英國人描述沙漠的落日、燥熱的天氣、出沒於夜晚的野生動物和尼羅河,為女人們讀阿巴斯時代的詩歌。用故意滿足殖民者對於他的幻想的方式來達到其目的,進行報復。然而回到村莊之後,他溺水而亡。「我」在他死後走進他的書房,裡面放著西方學術書籍、英文版的可蘭經、維多利亞時代的椅子和絲綢桌布(絲綢—印度—英國殖民的暗示)等。一切都是殖民者的遺產和象徵。
「我」走出剛回到家鄉時看到的那幅充滿希望的後殖民圖景,意識到,「我」看到的不是賽義德,而是從鏡子中看到了自己。當兩個人都終於回到故土之後,不僅無法再次融入故土,還發現自己身上已經刻滿了殖民者的痕跡。
殖民者的魂魄依舊在這片已經獨立了的土地上遊蕩著,搭載人們通往未來的鐵路是由英國人修建的,首都政府的獨立大廳是在倫敦設計的,多麼諷刺啊。賽義德嘗試在倫敦重獲主體性,國家也終於獲得了獨立,最终卻發現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關係並非是傳的、僵化的、永遠對立的,兩者非但不可被一刀割斷,還互為對方的一部分,互相定義,互相依存。
「我」的祖父雖年老,卻充滿活力、頭腦清醒,是故土靈魂的縮影,也一直是「我」在故鄉安全感和歸屬感的來源之一。在一次爭論時,「我」憤怒離開,祖父叫住「我」,「我」並沒有回頭。這是對於過去、對於傳統的不安和拒絕。不同於政治運動和革命中活動家們勇敢甩掉過去,擁抱未来的叙述,小說中的我其實搖擺不定,拒絕過去和傳統並未被描寫為一件易事。「我」無法決絕地一走了之,因爲要否定自己生長的土地是打破原有的情感結構的,這當然令人十分不安。
在這惴惴不安的感覺中,穿插著詩歌和景色,作者一次次用對夜晚(黑暗)和白天(光明)的交替來暗示過去與現在、傳統與現代、殖民時代與後殖民時代、北方(英國)與南方(蘇丹)之間的模糊界限。「我」到底是誰?應該成為誰?家鄉還是那個家鄉嗎?
小說還通過對性與權力、暴力與霸權、女性與婚姻生活的討論,試圖描寫後描殖民時代、已經獨立了的、屬於人民的土地上人們面臨的不僅是個人的也是結構性的身份困境。在這個充滿絕望的故事中,作者在结尾處給了一線希望,當「我」在河流中,處在南方與北方之間,在任由河流淹沒和活下去之間,「我」還是選擇了向他人呼救,想要活下去。賽義德的命運是死亡,而「我」的選擇是繼續生活,這展示了一種時代性的選擇和變化,先活下去,帶著這不適感、恐懼感繼續活下去,活下去就還有找到小時候的微風、熟悉的臉龐、祖父身上的味道等等一切曾帶來的幸福與希望。
這本書在歐洲出版之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無論是文學系的、歷史系的還是區域研究系的學生都會在這樣或那樣的課上讀到它。因爲他描寫的個人生活困境不僅僅是蘇丹或是第三世界人民的;也是近入後現代、面臨難民潮和民粹主義興起的西方人民所面臨的身份挑戰,我們與他者到底意味著什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真的是一道牆、一條移民政策可以决定的嗎?
在中東,阿拉伯與以色列、什葉派與遜尼派的長久對立是絕對歷史真相還是權力關係的產物?無論如何,普通的人們都將在這複雜的政治局勢裡面臨時時刻刻的、具體的、實在的生活困境和苦難。
作為局外人,在試圖理解他人生活時,也不該再將所謂文化差異作為一個結論來進行思考了,而是應該像小說中的「我」一樣,與不安感和陌生感共同生活,將文化和宗教差異作為出發點,在了解世界是緊密相連、國界線也並非天然存在的基礎上,通過建立我們與他者的聯繫来重新思考差異。
本文章獲得中東研究通訊授權轉載,微信公眾號ID請搜尋:MenaStudies。
封面照片:Photo by Bryan Minear on Unsplash






